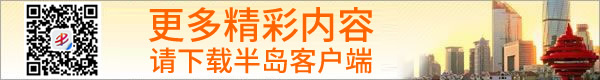?
作者:朱習(xí)之
“要吃一口嗎?”
她將咬下大半的粽子遞到我面前,淡黃色的糯米已是皮開肉綻,露出里面的雜餡兒,紅棗、蛋黃、花生、肥肉。我不假思索地抿下一口,有些發(fā)冷的米在我的口腔稍作停留,沙沙的,像是在吃普通的飯團(tuán),失去了糯米黏人的突出優(yōu)點(diǎn)。
可當(dāng)她詢問我好不好吃的時(shí)候,我還是昧著良心點(diǎn)了點(diǎn)頭。這種似是臨時(shí)湊數(shù)包出來的粽子,連家鄉(xiāng)正品新鮮貨拿來包粽葉的線繩都比不上。
家鄉(xiāng),家鄉(xiāng)的粽子是什么味道來著呢,我?guī)缀跬耆鼌s了。恍然間,我已有兩年沒有在家好好過一個(gè)端午了。
說這時(shí)間不長,也存在于五六年前的記憶中;又說這時(shí)間不短,也只是在我小學(xué)的時(shí)候。幾平米大小的廚房,我懵懵懂懂地看著母親忙上忙下,洗著粽葉,備著糯米,灶臺上的蒸鍋仿佛比我還要高一個(gè)頭,嗤嗤地像蒸汽火車般冒著白氣。洗凈曬干的粽葉被母親卷成了冰激凌圓筒,右手抓過一把糯米細(xì)細(xì)地倒下。在我的印象中,母親的手像是世界上最精確的量筒,甚至一粒米,一顆鹽粒,她都能把握得精準(zhǔn)無誤。她一面裝著糯米,一面絮絮著:“……米不能放太多,不然煮好了要膨脹的……也不能太少,要么就癟掉了。”之類的話,我記不太清了,饞蟲早已把我的思緒勾到了千里之外。這時(shí)母親總會(huì)佯裝懊惱地嗔怪一句:“多學(xué)點(diǎn)手藝!不好好聽……”裝好了糯米,她又用線繩,教粽葉把零散的糯米包得嚴(yán)嚴(yán)實(shí)實(shí),我想她給我裹外套的手法怕是從中演變來的吧。涉及到打結(jié)的活兒我就很苦手了,無論過了多少年,就算是母親手把手一步一步教,我到至今依舊是一竅不通。所以在這種時(shí)候,我只能靠賣乖來避免母親的嘮叨,主動(dòng)將一個(gè)又一個(gè)成型的粽子扔進(jìn)熱氣騰騰的蒸鍋,擺成整整齊齊的一圈,像是在列什么方隊(duì)。
粽子蒸的很快,包裹著粽葉清香的結(jié)實(shí)圓潤的糯米逐漸破裂開來,變得粘稠緊湊,滿滿浸入豆沙餡料香甜的滋味。美美地吃上一頓粽子,大概是人生中極為享受的一件樂事了。唯一可惜的是不能吃太多,母親說糯米黏胃,與元宵同理,除了一頓不能吃多,還有早餐不能吃粽子等土說法。現(xiàn)在身處他鄉(xiāng),再無這類規(guī)矩條款的束縛,可我也再?zèng)]品嘗過那般美味的粽子了。
包粽子剩下來的線繩呢,母親通常會(huì)再找來幾根不同顏色的,巧手一撮一編,又成了端午的第二項(xiàng)傳統(tǒng),五彩繩。細(xì)細(xì)的幾股繩系在手腕上,對幼時(shí)的我像是栓了一條鐐銬那么難受,粗糙的觸感讓我無論如何都不覺得自在。母親則是一邊為我系上死結(jié),一邊煞有其事地說:“五彩繩會(huì)保小孩子歲歲平安,在端午節(jié)后的第一場雨要記得摘下來讓它順著雨水流走,這樣一年的霉運(yùn)也就隨之流走了……”這些說法我是從來不信的,但母親打的結(jié)我向來是不動(dòng)剪刀解不開的,只能作罷。于是又在大快朵頤一頓粽子后天天盼著老天爺早些下雨,哪怕只是飄幾點(diǎn)雨滴,我都會(huì)迫不及待地剪短那條枷鎖,看它隨著小小的河流飄去遠(yuǎn)方,無影無蹤。而今天我才悄然察覺,順流而去的不只是五彩繩和霉運(yùn),還有童年的時(shí)光歲月。
再剩下來的繩呢,母親是絕不浪費(fèi)的。找些包裝盒,拆成小塊,左折右折,又成了一串串粽子形狀的掛墜。那些繩子好似長在母親的手上般,那么靈巧,那么嫻熟。她像創(chuàng)造萬物圣靈的女媧,無數(shù)巧奪天工的藝術(shù)品從她手下誕生。
掛墜就系在走廊的拐角處,如風(fēng)鈴般叮叮作響,直到被夏日鋪天蓋地的蟬鳴所取代。
最遺憾的是,我從未看過端午的賽龍舟活動(dòng),對它的印象也僅限于語文課本。兩條長長的龍型船,幾十個(gè)人奮力劃動(dòng),領(lǐng)頭的人敲著鼓,喊著有節(jié)奏的號子,岸邊的群眾大聲吶喊助威,看著兩條龍舟朝著一望無際的地平線駛?cè)ァ?br>
龍舟只會(huì)向前進(jìn),無法回頭。
它載著我順著時(shí)光水流的方向順流而下,卻忘記了載上那香噴噴的粽子,那簡陋卻樸實(shí)的五彩繩,和從我指縫間悄然流走的,有母親陪伴左右的童年。
[編輯: 劉曉明]